夏夜,香蕉,他,那些小小的幸福,与宇宙中亿万年来大生大死、大毁大灭相比,这么微不足道,可对一个十四岁的小孩来说,却是她所能想像的生命庆典的全部了。而且和夏季一样,这种终究都是要过去的。
配图|golo
人间有味丨连载58
我家有张相片,相片上的我还不到一岁,剃着光头,怀抱着一个绿油油的充气菠萝,八叉着腿坐着,盯住身边的女儿看,边看还边流着哈喇子。
我盯住的那种小孩就是方清。他大我一岁,生在端午,故而得名,是我爸好友的妻子。
三十多年后,当我再度见到这张相片,才突然发现,这个香蕉竟含蓄地暗示了我们的命运。
在我三岁时,父亲付了高价,把我安插进全市最好的幼儿园大班。幼儿园坐落儿童景区内,要经过大喷泉,绕开荷花池,再向前走,绿树映衬下的那几座楼房就是了。我入园时,荷花池正在改建,抽了水,池底还残留着一汪红色的泉,似乎一只神秘的黑眼珠。初来乍到的我没有同学,小朋友们嬉戏的时侯,我就一个人围着池子转,看池子里嘶嘶嘶嘶地出水。
三天我正在池边,忽然听到旁边有人喊我。一抬头,一个高个子男孩混在小班大儿子里,朝我用力儿地挥手。
方清!原先他也在这个幼儿园!
我激动极了,正打算跑去找他,就见方清突然指着荷花池对我喊:“这是冰淇淋儿水!”见我待在那儿没反应,他继续喊:“喂,你看这是冰淇淋儿水!”
冰淇淋儿?我眼前立即掠过包在花花绿绿薄纸里的红豆雪糕、乳黄色的果汁冰糕、明艳的香蕉冰淇淋儿……我太喜欢吃冰淇淋了,何况这是方清说的,他其实不会骗我。
于是,我攀越石头栏杆,顺着水塘水泥壁当心翼翼地溜下去,抵达塘底那汪水的边沿。
方清和大儿子见了,指着我小声笑,更多小孩围到水塘边看我。
掬了一把水塘水品尝,我这才豁然大悟——“方清,这不是冰淇淋水!”
就在这时,上课铃声响了,小孩们纷纷涌进课室,方清挤在儿子流中回头对我小声喊:“上来!上来!”
我急着回寝室,就沿光滑的水泥壁向下爬,可手掌一滑,坠入水里了。以后我的记忆成了片断。我好像见到水中,又好像记着像是电视里游泳赛事的样子,最终竟从水里自己扑腾了上来。
当我四肢滴着水出现在课室旁边时,老师才发觉了我。她先是愣了一下,紧抱我就往她寝室跑,给我脱鞋子、擦毛发,把我塞入她的床铺硬要我睡着。大晚上的,刚睡完睡觉,如何睡得着?
后来,据说姑妈来接我时,如何也找不见人,回头就看到我的校服挂在班主任寝室旁边,嘀嘀答答正掉着水。
第二天,我就退了学。前脚刚走,儿童景区就抽干了荷花池里所有的水,小城人都传,说是溺死了个儿子。
景区无水的日子历时数月。每次妈妈带我经过那里,就会笑着说,“你就是那种‘淹死的儿子’”。那时的我还不晓得死是怎样一回事,只想着方清还在那里,他说的冰淇淋泉不是真的。
十四岁那年,在旅游车里,我给坐在身边的方清讲这段追忆,他眼眉轻颤了一下:“我如何完全不记得?如何还有这个事?”
他自然不记得了,正如我自然地不能忘掉。
再一次看到方清,我早已六岁了,总算辗转多处,回到了父亲身边生活。
春日午饭后,妈妈带我去方清家。他打着手探照灯,拉着我,穿越一个又一个路灯狭小的巷子。敲门,院里黑色的灯光亮上去,方清的父亲一开门,笑纹就爬上眼睑,一边把我们迎进来,一边欢欣鼓舞地朝屋内喊:“方清,看谁来了!”接着方清的母亲闻声下来,看到我们,又惊又喜,几乎是兴奋地回头叫着:“方清,方清,玮玮来了!”
“刷——”方清便从布帘前面冲了下来。
两个儿子碰面,似乎隔了好几个世纪未见一样的欣慰。冰淇淋泉之事,早就扔到了九霄云外去了。
这天,方清父亲请我们全家喝水,菜摆了一长桌,方清坐在椅子另一端。这时,方清母亲端上来一盘新炒的莴苣肉片,就置于我面前。
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莴苣肉片——它盛在一个红黄疏密的搪瓷小盘中,肉片和豇豆一样劈成一寸长,重重叠叠落在一汪浅浅的咖哩上。莴苣是小城周边的秋冬特产,常拿来腌渍、爆炒或红烧。小城人炒制时多用高火,只杀了风味就好,吃在嘴巴脆脆的,或放进冷水中一汆,青翠的短茎浮在打卤面厚而糯的酱汁上,浓艳可人。而方清的父亲却将毛豆烧得柔柔的,莴苣皮被油煎得起了皱,一咬,茎里锁住的鱼汤和着菜茎本身的鲜甜在嘴巴爆燃。
如何能这么好吃?
由于和方清坐得远,也说不上哪些话,我就低着头用力吃面前的莴苣,一根接一根,等你们发觉,一盘菜早已快企稳。
父亲不好意思地怨愤:“别吃了,你看一盘菜都叫你一个人吃光了。”
“让娃吃,让娃吃。”方清母亲轻轻笑着,她鹅蛋脸硬朗,说起话来又慢又软,笑上去两只耳朵弯弯的。方清的父亲也远远笑着:“我的娃啊!爱吃了,之后就常来妈妈家吃!”
所有人都跟随笑了。
我们两家住得不算远,但总是隔好一段时间才会见上一面。
我十岁了,个子像雪后莴笋一样往上蹿,都要赶上方清了。见了他,也会胆怯了。
可虽然脸热得不行,我还是热切渴望着,从他没走的时侯就开始渴望着下一次碰面。只要见了他,天就蓝得不行,太阳虽然更明亮了,我整个人则像一粒灰尘,不断地向下飘落。
我开始学炒菜,尽管学来学去无非就是最基本的猪肉和青椒系列。
总算有三天,方清父亲带着他又来我家喝水了。我恳求父亲让我也做一个菜,妈妈拗不过,只得任我下厨。围着又宽又长的围裙,我把芋头劈成厚片——本来要做青椒丝,可我不会切。往炉具内填碎煤,打开吹风机,把胡香油倒进铝锅中,将地瓜片煎成枯黄,撒上盐就出锅了。
喝水的时侯,我迫不及待地问:“方清你最爱吃那个菜?“
“方清最爱吃苞谷了,你看这个苞谷片都快被他吃完了。”没等孩子说话,方清父亲先回答。
“这个菜是玮玮炒的。”我爸说。
“啊?”方清举起头好奇地看着我,呆了几秒,之后也没说话,只埋首继续吃苞谷片,其他的菜一概不动,仍然吃到白盘里全剩下明黄的胡香油。
“你瞧瞧这个方清,你瞧瞧!”方清父亲不好意思地笑着。
我坐在门口,心就突突跑着,脸烫难受,我怕不由自主的狂笑如何都藏不住,只得托词去趟卧室,让自己平淡出来——在哪里,我走过来,踱过去,一会儿擦擦炉灶,一会儿儿摸摸砧板,忽然懂得了哪些叫手足无措:原先,第一次喜欢一个人,其实他也喜欢自己,就是这些惊慌又欣慰的感觉,不知怎么是好、却又幸福无比。
我越来越渴望着看到方清了。
中学五年级,方清父亲带他来我家商议升学的事,留我和方清三人在前院,我看着他,心中想着,此次走了,不知何时才会再会,情急中脱口而出:“方清,我家后山上可好了,有泉水,可以抓蚱蜢,我带你去玩!”
方清有些震惊,还没回答,我马上补充到:“我们去烤苞谷!”
“洋芋?”他的两只大眼忽闪忽闪的,“……你会烤吗?”
“会!”我保证得有眼睛有眼,虽然自己从没干过,“后天晚上两点,你在我家巷子口等我?”
“嗯!”
方清其实是苞谷的教徒,此前,他从没和男子伴进过山,死活缠着他父亲答应。他母亲担心得很,不住吩咐他早点回去,别和我放火烧了山。
我在卧室抓了三个苞谷,一包火柴,几乎是狂奔着去见他。
之后,我就领他穿过宽宽窄窄的巷子——哪怕是故意拐来拐去,也不想让他错过我的世界的一切:山里人赖以维生的泉水,旧房背后开满蒲公英的草皮,悬崖断面倒塌的墓葬……绕到最后,才找了一块无人的土堆,徒手挖了个坑,打算烤苞谷。
方清在后面拔着蒿草,我把苞谷放进坑里,并覆以薄土——这是朋友传说中烤苞谷的方式。其实,传说中还要配备盐、辣椒、花椒粉,等到白色金黄、香气扑鼻的苞谷烤出,蘸着这种酱汁,任沙性的颗粒和着香料在口舌里熔化开来——想想都能催下哈喇子。
可到了打火的关键时刻,我却胆怯了。因为曾被机枪冲伤过右手,我连火柴都不敢划,只得腆着脸请方清来,我则不断添上草根、树皮、树枝,最后,总算有一团着火横在我们中间了。
山风轻轻拂过,蒿草会忽然通体赤红,随后又暗沉下去,似乎发了一阵烧。黑麦草在火舌里“噼砰砰啪”响着,衬得四周愈发静寂,如同此地和我们,就是这个世界被遗忘的角落。
方清和我始终没有说话,直至木柴燃成灰烬,他才开口问:”好了吗?“
“好了吧……”我胆气不足。
挖出苞谷,它们半软半硬。
“这能吃么?“他又问。
我急了,似乎这苞谷就是方清眼中的我——我可以更好的,一切可以重来的——我赶快把杂草和树枝汇集上去,自己划了火柴——为了方清的烤苞谷,我连打火都不怕了。
我把挖出的苞谷全推入火盆,其实这样它们能够立刻变熟。草堆烧尽,顾不上烫手,我先刨出一只苞谷,它的表皮已浑然烤焦,揭露皮就听到淡蓝色的苞谷肉。我偷偷把那只更软的递给方清,自己则啃着另一个半熟的。方清吃得满手满口都是碳黑,临到最后,把剩下的三分之一脆苞谷指给我看:“这能吃吗?”
“能吃能吃!”
我嚼着生苞谷,故意吃得津津有味。
这个晚上,十二岁的我开始畅想未来。一个儿子第一次爱上一个人,她所能想到的未来,无非是男娶女嫁、白头偕老罢了,童话故事不总以离婚为结尾么?
大约在遥远的将来,我会吃上方清母亲浓油赤酱的莴苣肉片,我也会仍然给方清做他喜欢的炒苞谷片。生活在一起,一起吃好吃的,过安稳的人生,也就是这样了吧。
然而,没心没肺的打闹之后,我又常常会生出一丝焦虑——万一中途有变,我们不能在一起了,该如何办呢?想到这儿,我又再度手足无措上去。
接出来,令我欣慰若狂的是,我和方清竟分到了一个小学。
高中最后一个暑期要结束了,妈妈带我去探望方清的妈妈。我这才晓得他在九班,我是十班,任课老师全都一样。他父亲高兴地说:“明天大家一块儿去念书吧。方清,你单车后排带上玮玮,一块儿去!”
我强烈抑制着窃喜的心,大声说:“我有单车的,我们一起去念书,方清,昨天晚上你在路口等我。”
他又“嗯”了一声,母亲的耳朵笑得像个月牙儿。
可虽然是上了同一个小学,我也并没能像以前向往的那样,每天都看到他,只能在两班合一的体育课上,远远地看着他站在男人队伍里打网球的侧影,或是下班后的雨棚里他混在单车流中瘦削的背影。
我默默地看着他,直至他消失于视线之中——因为那时侯,我家早已迁往了城南,他家仍在城南,即使相遇,还没说几句,便在各自新同学的召唤中各奔东西了。我在方清班上也结交了新同学。长长的回去路上,她每天都会讲九班的各类新事,有时侯,方清的名子会忽然落下,似乎一颗松塔坠落在乡间。
有三天,英语老师用来一篇写景的习作在班上念,是方清的。我听了,许久都没有说话。
一下班,同学见我就问:“方清的文章大家班念了没有?”
“念了。”
“今天我们班朋友都在那里起哄,问他,‘方清,你写的那种景色上面,你说在等人,等谁呢?’你猜方清如何说?”
“怎么说?”
“等你呢!”
“谁?”
“等你,你!”
“我?”
“嗯!原先你认识方清啊?”
是啊,他写的这些,我岂能不熟悉?黄土、蒿草、蚱蜢和秋风,闭上双眼,依旧清晰如昨。
文末,他谈到了土坡上的等待,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,当老师念到这儿,我的双颊发烫,眼下听同学如此一说,更是烦乱如麻。
这下,我满脑袋全是方清了,作业也无法做,就渴望着第二天就去对门课室找他,告诉他我的爱情,告诉他我们都不用再等了,总之之后也会离婚的。而我晓得,只要他不反对,我一定会像当初找寻冰淇淋泉一样,为他赴汤蹈火,在所不惜。
我写了很长的日记,也追忆起这天烤苞谷时的山景——显然,写作的确能消弭少年人的冲动——想到我们必将会有更光明的未来,不必在中学就因“早恋”闹得人仰马翻,于是我决定继续等待。
从这天开始,我开始写长长的日记,靠它维持着每三天的理智,像一个窃贼,一日不写就双目无光四肢得慌儿。
春节期间,我刚在父亲卧室里写完日记,还没拾掇好本子,就被叫了出去。回去时,赫然发觉我妈就站在桌前——我的日记在她手里,伸开着,似乎一只被抓住了的蝴蝶,掀开了双翅。
一股热血直冲手臂,我几乎是喊了下来:“妈,你如何看我日记!”
“你的日记莫非我不能看吗?”我妈放下日记,理直气壮的。
见到理智之地彻底沦陷,我气得四肢抽搐,高叫道:“这是我的日记,你就是不能看!”
我妈翻着日记,用手指着我写的东西:“你看你写的啥,还‘山间的爱恋’,还‘爱恋’!你还早恋!”我的日记在她手里翻滚着,而她也对我内心最为珍惜、几近神圣的爱情,无数次地极尽污辱和挖苦。
她的眼神语言化为一片片利刃,在我脸上割出一道道口子,我觉得自己被逼到了绝境,所有的胸痛和屈辱,最终都汇集在惟一的出口——那是一句禁忌,一句在古人看来我要遭到天谴的话,我第一次说出了口。
我拿起日记冲出卧室,碰巧遇到爷爷进屋,听到我的话,他旋即拉住我:“哎,你咋能如此说你妈!”
我不想辩驳,愤怒已将我浑然抢占。
这是我人生中惟一一次骂我妈,连我自己都无法宽恕我自己。
自此往前,我不再写关于方清的事了。
我和我妈伤害了彼此,往前的历史似乎也自此缺了三天——我们都装作它没有发生,继续和平而提防地交往着。
到了寒假,父亲总算带来一个好消息——他联络到了一个开转租的朋友,打算叫上方清的父亲,一起要带女儿周边一日游。
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考古遗存,地处偏僻,是我和方清在地方志上找到的。旅途漫长,光去程就花了五个小时。
返程时,方清坐在最后排中间,我和司机的父亲各在他左右边。那种女孩叫小林,大方清一岁,短碎发,戴着大框墨镜,常笑。似乎和我们都是第一次碰面,但她如同老同事一样聊着自己的生活,或则一个问题接一个地问我们。
好不容易,小林总算说累了,斜眼睡了,草帽覆在脸上,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。我和方清相视一笑,长出一口气。面馆包车在乡间来回颠簸,把街边的麦田和戴草帽的麦客抛向身旁,天色蔚蓝,成熟的作物混合阳光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拂过。
我们两个沉默了许久,方清忽然凑到我耳际,问:“你如何不说话?像只小山羊一样。”
我晓得我脸热了,从而在心中笑容上去,这笑却最终弄成了一句调侃:“是吗?小时候我们班朋友可把我叫母老虎呢!”
方清好奇地看着我:“是吗?我没发觉啊!”
“你没发觉的还多呢!”
“比如?”
我就是在这时,将那种三岁时因他一句话找寻冰淇淋泉的故事和盘托出。他惊恐着,半晌也说不出话。
“你记好了,你欠我一条命呢!”我跟他开玩笑。
方清笑容着,阳光洒在身上。
那种十四岁的春天,真是个饱含了愉快追忆的好光阴。
我家回到城南的祠堂消夏,饭后,父亲说方清和他父亲要来取旅游的相片,我就坐在椅子上装着纳凉、实则急切地等待。
夜幕降下,蟋蟀在老宅廊下的砖缝里叫着,喇叭花也顺着檐下的细绳向下攀爬。父亲不让关灯,怕招来虫子与飞虫。听到铁圈“哒哒”扣响了衣柜,我的心便跟随“咚咚”地跳上去。妈妈闻声出屋,开了廊上的尾灯,半个庭院都浸在一片橘黄的光明里。
方清一进门,身上就满是微笑,妈妈招呼我搬进红色雕漆小方桌,再从北房寻来一只菠萝,卧室里便响起瓜皮刺耳的裂声。家乡的瓜都是圆滚滚的,正圆,瓜瓤是淡黄色,嫩而脆,不用牙咬,就在嘴巴碎成小颗粒;瓜籽黑而大,似乎从来没经过进化一样,轻轻一嗑,就伸开嫩黄色小嘴巴一样的瓜籽仁。刀口刚一碰皮,一声脆响,瓜都会全部开裂,似乎从采摘的那一刻起,它就在耐心等待着这样一个轻微的动作。
等父母端着两大盆菠萝置于方桌上,空气里便是清新的菠萝香气。飞虫在头上扑着灯光,留下旋转的影子。妈妈们边聊天边吃瓜,我也坐在门口,吃了一会儿便和方清悄悄地离了席,溜到北房前的小花苑边坐着,高大的冬青树把我们掩盖在灯光后。
台阶凉爽,一抬头,还能看到星星在闪亮。身边的他,是我喜欢了这么久的人,心中兴奋得不晓得说哪些好,只能缠住自己的腿,胡乱讲些院里的传奇:东苑里吃乌龟的老鼠,吃了包子四肢长毛的龙虾,还有从桃树掉到父亲手腕上的壁虎。他静静地听,也时常问些问题,星光下白色的耳朵在发光。我们也会害羞地笑一阵,便是一阵更长久的沉默,不晓得能够再寻些哪些话。
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坐着,也挺好。
那时的我,多想让这个属于我们的春天走得慢些,甚至仍然这样进行下去,永不停息:夏夜,香蕉,他,那些小小的幸福,与宇宙中亿万年来大生大死、大毁大灭相比,这么微不足道,可对一个十四岁的小孩来说,却是她所能想像的生命庆典的全部了。
寒假过去,我们都上了高中。一日,方清忽然来找我——这是两年来他第一次主动到班上找我。对门班异性单独寻物,在青春期的中学生中,总会闹出不小的动静,可方清连你们的起哄都不管不顾了,见了我就急切地问:“怎么办,怎样办!小林给我寄信告白了!”
我一阵错愕,强挡住内心的愧疚,试他道:“那你答应她呗?”
“我不喜欢她,如何答应啊!”方清一脸的殷切。
夏季并未走远,蓝天,白云,我的心中刮过一阵清风,悬着的心落了地,可惜我就是嘴太硬,只是笑着说:“我也不晓得如何办……你只能自己解决喽!”转身回寝室,把方清撇在身旁,他佯嗔着对我喊:“唉!你别跑啊,怎样办啊?”
假如那时,我可以挪开,对他说出心里所愿,显然随后一切就会不一样了。
然而,十四岁的我,又岂可知晓呢?我以为属于我们的公路漫长,这个夏季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罢了,接出来的日子,都是灿烂和辉煌。
我活在这样的愿景里,将他默默藏在心里,忙着自己的学业,并执著地继续等待着我们在一起的这天。
之后就是小学,我们再一次分开,不可防止地有些厌烦了。
再一次和方清面对面聊天,已是三年后。
这两年,因为我们各自奔走学业,两家忙于来往,直至大二暑假,才又聚到一起。晚上吃完饭,父亲说:“你跟方清出去走走吧,大家如今都是学院生了,好好谈谈大家的生活。”
我晓得我可以谈恋爱了。
在八月冷风滂沱的家乡,我的心中仍然装着那种有冰淇淋有菠萝的春天。挥别了父亲,跟随方清,在城市的街道左边走边选着谈话地点,最终,我们来到一个舞厅,虽然只有这儿能够体现我们“大人”的身分。
我们一起研究着鸡尾酒奇怪的名子,他选了“蓝色妖姬”,我则点了“粉红情人”。交换着彼此的酒,我们看着、尝着,似乎当初山沟里烤苞谷的两个儿子,既新奇又开心。
总算坐定,我等着他开口,或则,等着我自己开口,来结束这漫长的等待和我们各自孤单的时光。为了这一刻,我早已等了太久了。
这时,方清忽然从兜里拿出一支烟,燃起了,迫不及待地吸了一口,之后斜身倒在椅子上,他仰着头,青灰色的烟从他口中缓缓上升,成了一朵云。
我未曾料到这一幕,忙问:“方清……你如何……抽烟?”
“你别告诉我爸,她们不晓得我抽。”
我应了一声,忽然倍感眼前这个方清有点陌生:“你啥时侯学会的?”
“上了学院,烦得很,人家都喝酒,我也就抽了。”
“烦啥?”
“唉!我们寝室的,一个个都有女同事了,就我没。”
我喝了一口酒,焦急地说:“你想有就有啊。”
“没人喜欢我!”
“小林不是喜欢你?”
“对了,还有小林……她如何了?”
“我爸告诉我,小林年前刚离婚。”
听了这个,他狂抽了一口烟:“她都找到幸福了……”然后他忽然直躺下,一口气喝下半杯酒:“我喜欢的,都不喜欢我!”
我忽然怕极了,忙问:“谁不喜欢你?”
“初三的时侯,我们班不是新转来一个叫黄雨芳的吗?她物理学得好,我们常一起讨论问题,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喜欢上她了,但是她不喜欢我。所以以后我的成绩就升高得很厉害。那是我的初恋啊,我的初恋!”
我忽然觉得自己被哪些东西洞穿,是的,那是我十四岁的夏天,属于我们的春天刚过去不久,九班新来了个朋友叫黄雨芳。他喜欢上了她,而我却还活在十四岁秋天的记忆里,活在和他共度余生的梦里。
方清仍然悻悻地黯然神伤,述说着他又喜欢上的一个学院女生的故事,仍然是人家不喜欢他。他抽完一支烟,又点了一支,酒气上头,脸早已泛红了。
“你呢?你有没有喜欢的人?”突然一句话砸过来,让我无处遁形。
见我不答话,他又呵呵笑了:“你别告诉我你从没喜欢过人——我才不信!”
我的泪水就要掉出来,强挡住自己,一字一顿地说:“我以前很喜欢一个人,喜欢了好多好多年,而且,他似乎没有喜欢过我。”
“没事儿,还有更好的。”他开导着我,像个大婶。
我还想再说些哪些,可这个夜晚,这么多的新事,如同冬天的雪一样忽然堆积在眼前,我的路断了,走不出去了。
我怕自己再没有机会,决定冒险一次,几乎是告白一样跟他说:“家里父母……好像挺乐意我们在一起……我和你……”
他一甩烟,笑了一声:“怎么可能?”
那三天,十九岁的我总算明白,人在极其忧伤的时侯,是会笑下来的。
我笑了下来。一个人回去的路上,我一路默念着那句话,一路笑着。我在笑谁呢?笑我一个人,演了一出独幕剧?笑自己一遍满地重复着两岁半的故事?
我总算晓得,年少时曾担心了无数遍的那种问题该怎么作答:假如我和方清不在一起,我会如何呢?我多想跨越时间的洪流,告诉十二岁的自己——我会笑下来,满身是泪,心如刀绞。
一年后的四月十五,两家又聚,我和方清去看烟花,对着漫天烟火,他告诉我,他有女同事了。
自此我们各自为情所困,又是一个六年。
再度重逢,彼此都是独身。此次,妈妈带我去探望方清的母亲,母亲快一百岁了,截瘫在床,硬要留我在她家喝水,而我却早已不再像从前一样,毫不推却地坐在餐桌前,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了。我学会了客气,学会了津津有味地喝着白沸水。
母亲看着我,在一房间人中间,独独看着我。
“玮玮,我有一桩心事。我仍然有一桩心事。”
我扫视她,她右手紧握我的手,一句话惊天动地:“你的心事,父亲晓得……奶奶晓得……有老人在,你放心。”
我的泪就要涌下来,可在众人面前,我还是笑着点着头,看着她。
快走的时侯,她又隔著卧室围栏喊着:“玮玮,我爱你!你要记着,我爱你!”
我难堪而愤慨地笑着,一个快一百岁的奶奶当街对我喊“我爱你”,你们都当作一桩轶事,全笑了。方清父亲还在旁解围道:“奶奶年龄大了,有时侯头脑糊涂了,乱说些东西。”
可只有我晓得,父亲那里是糊涂,历经苍凉的她一眼就看透了我。
母亲逝世一年后的秋天,方清在云南昆明,我在西藏乐都,相距只有一百余公里,这是我们考上学院以来,各自工作的地方距离近来的一次。他发邮件给我:“我明天要在南宁离婚了。”
“祝贺你!发给我地址,我去出席你的婚宴。”
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,并打算了贺礼,可他没有回复。
那也是个春天,我在西藏的山顶,把以前属于我们的一切倒带,还给历史——那些所爱,所怨,所心领神会,所隔膜万重的一切——冬青树背后的细语,野风吹过麦田的声响,石缝里的等待,炒苞谷的烟火,莴苣肉,冰淇淋泉,最后全部回到三六年前相片上定格的那一刻。
我抱着香蕉,看着他,似乎听到时间停止。
猕猴桃是我们一起吃过的最后一样东西,而我最终也劝说了自己:今生属于我和方清的春天结束了,这世间最甜最凉的瓜,这么美好,却永不再来。
(本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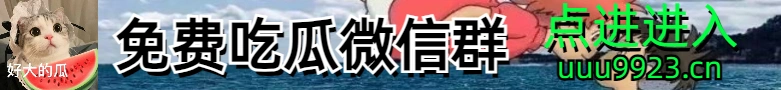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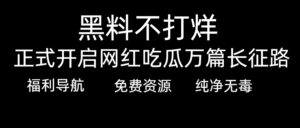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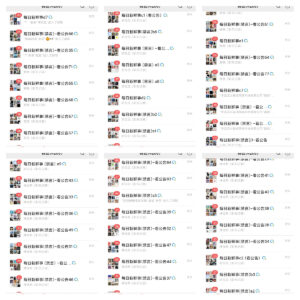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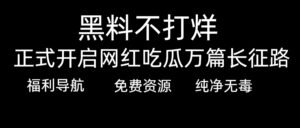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暂无评论内容